陳子昂簡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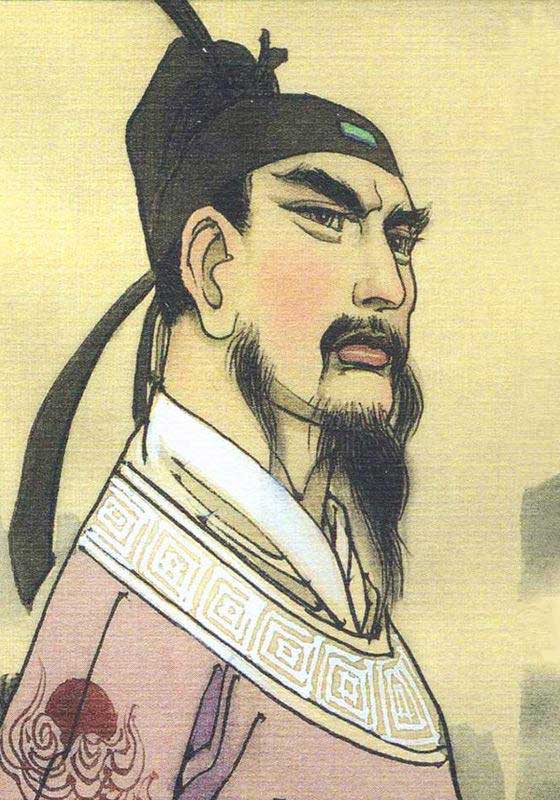
陳子昂(約公元661~公元702),唐代文學家,初唐詩文革新人物之一。字伯玉,漢族,梓州射洪(今屬四川)人。因曾任右拾遺,后世稱為陳拾遺。光宅進士,歷仕武則天朝麟臺正字、右拾遺。解職歸鄉后受人所害,憂憤而死。其存詩共100多首,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《感遇》詩38首,《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》7首和《登幽州臺歌》。
〔? 陳子昂的詩文(6篇)陳子昂的名句(4條)〕軼事典故
伯玉毀琴
陳子昂第二次落第,適一人賣胡琴,索價百萬,豪貴圍觀,莫敢問津,陳子昂擠進人群,出千緡(古代一種計量單位)買之。并于次日在長安宣陽里宴會豪貴,捧琴感嘆:“蜀人陳子昂,有文百軸,不為人知,此樂賤工之樂,豈宜留心。”話完即碎琴遍發詩文給與會者。其時京兆司功王適讀后,驚嘆曰:“此人必為海內文宗矣!”一時帝京斐然矚目。
獄中卜命
盧藏用《陳子昂別傳》云:“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,聞其家有財,乃附會文法,將欲害之。子昂慌懼,使家人納錢20萬,而簡意未塞,數輿曳就吏。子昂素羸疾,又哀毀,杖不能起。外迫苛政,自度氣力恐不能全,因命蓍自筮,卦成,仰而號曰:”天命不佑,吾殆死矣!"于是遂絕,年四十二。
人物生平
少年時期
陳子昂幼而聰穎,少而任俠,年十七、八,尚不知書。后因擊劍傷人,始棄武從文,慨然立志,謝絕舊友,深鉆經史,不幾年便學涉百家,不讓乃父。
兩次落第
高宗調露元年(679年),懷經緯之才的陳子昂,出三峽,北上長安,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習,并參加了第二年科舉考試。落第后還鄉。回故里金華山研讀,“數年之間,經史百家,罔不賅覽。尤善屬文,雅有相如、子云之風骨”,為他后來革新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永淳元年(682年),學有所成的陳子昂,再次入京應試,仍不為人知。
得到重用
文明元年(684)進士及第。
陳子昂生性耿直,關懷天下,直言敢諫,一度遭到當權者的排斥和打擊。三十八歲辭職還鄉,后為奸人所害。但因其文“歷抵群公”,得罪權貴,不為所用。不久唐高宗病逝于洛陽,武則天執掌朝政,議遷梓宮歸葬乾陵。陳子昂聞后,上書闕下加以諫阻,武則天看后,嘆其才,授以麟臺正字,旋遷右拾遺。垂拱二年(686),萬歲通天元年(696)兩次從軍北征。
受讒被誣
陳子昂北征,積極反對外族統治者制造的分裂戰爭,多次直言進諫,不但未被采納,卻被斥降職。一度遭到當權者的排擠和打擊,壯志難酬的陳子昂三十八歲辭職還鄉,后被奸人陷害,冤死獄中,年僅四十一歲。
相關事件
(一)
陳子昂其詩風骨崢嶸,寓意深遠,蒼勁有力,有《陳伯玉集》傳世。陳子昂青少年時家庭較富裕,輕財好施,慷慨任俠。成年后始發憤攻讀,博覽群書,擅長寫作。同時關心國事,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樹。24歲時舉進士,官麟臺正字,后升右拾遺,直言敢諫。時武則天當政,信用酷吏,濫殺無辜。他不畏迫害,屢次上書諫諍。武則天計劃開鑿蜀山經雅州道攻擊生羌族,他又上書反對,主張與民休息。他的言論切直,常不被采納,并一度因“逆黨”反對武則天的株連而下獄。垂拱二年(686),曾隨左補闕喬知之軍隊到達西北居延海、張掖河一帶。萬歲通天元年(696),契丹李盡忠、孫萬榮叛亂,又隨建安王武攸宜大軍出征。兩次從軍,使他對邊塞形勢和當地人民生活獲得較為深刻的認識。圣歷元年(698),因父老解官回鄉,不久父死。居喪期間,權臣武三思指使射洪縣令段簡羅織罪名,加以迫害。冤死獄中(沈亞之《上九江鄭使君書》)。今天射洪縣城古城墻名為“子昂城”,街道有“伯玉路”等名稱實為紀念陳子昂。陳子昂的詩歌創作,在唐詩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績。盧藏用說他“橫制頹波。天下翕然質文一變”(《陳伯玉文集序》)。宋劉克莊《后村詩話》說:“唐初王、楊、沈、宋擅名,然不脫齊梁之體,獨陳拾遺首倡高雅沖淡之音。一掃六代之纖弱,趨於黃初、建安矣。”金元好問《論詩絕句》也云:“沈宋橫馳翰墨場,風流初不廢齊梁。論功若準平吳例,合著黃金鑄子昂。”都中肯地評價了他作為唐詩革新先驅者的巨大貢獻。但他的部分詩篇,還存在著語言比較枯燥、形象不夠鮮明的缺點。
(二)
父親的去世,給陳子昂以莫大的打擊,然而,更大的打擊還在后面。陳子昂老家所在的射洪縣縣令段簡是個貪得無厭的小人,他聽說陳家錢財富足,就心生歹意,圖謀勒索。陳子昂家人給縣令送去了20萬緡,尚不能滿足段簡的胃口,沒有滿足的段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將陳子昂打入了南監。
據說,陳子昂在獄中曾經自己給自己卜過一卦,卦相大兇,陳子昂驚曰:“天命不佑,吾殆死乎!”不久,他果然死在獄中,時年42歲。
這是《唐書》上的記載,但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因為一直到死,陳子昂都是未解職的朝廷諫官,不知當地縣令的“勇氣”何來,居然敢敲詐“國家工作人員”,以至于讓陳子昂冤死獄中,這一直是一個謎。后來,有人說是因為陳子昂在朝做官時曾開罪于武三思,所以武三思才指示當地的縣令如此折磨陳子昂。這似乎也不太好理解,因為武三思如果想收拾陳子昂,根本用不著搞得這么復雜。
不論怎樣,陳子昂就這樣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蓋棺論定,新、舊《唐書》給予他的一致評價是“褊躁無威儀”。所謂“褊”,意即狹小、狹隘;所謂“躁”,意即性急。“褊躁”用在陳子昂身上,也許比較合適。
陳子昂的一生其實就是褊躁的一生,從自我炒作,到大拍武則天馬屁,其實都是陳子昂褊躁的表現。但是,陳子昂卻有一件十分得意的事情,此事載于《唐書》之中。
某日,武則天治下發生了一樁轟動一時的謀殺案。被殺者是御史大夫趙師韞,他在外出公干途中被人殺死于一家驛站。兇手是同州下邽(今陜西渭南)人徐元慶,當時徐的身份是該驛站里的一名服務人員。刁民殺高官,這顯然具有十足的爆炸性,整個帝國的注意力都被吸引過來了。
為什么這個小服務員要殺害朝廷要員呢?標準答案是徐元慶為父報仇。原來,趙師韞曾任下邽縣尉,我們知道,縣尉在古代是縣令的屬官,專司當地的治安工作。徐元慶的父親因為犯罪被趙師韞正法。不久,趙師韞升任京官。徐元慶為報殺父之仇,隱姓埋名,到一家驛站做起了服務員。因為他心里清楚,這是他可以接近趙師韞的唯一方法。終于有一天,趙師韞為公事出差來到了徐元慶所在的驛站,徐元慶抓住機會,干凈利落地干掉了趙師韞,報了殺父之仇。
徐元慶到底是孝子還是兇犯,該殺還是該予以表彰,這在當時引發了激烈的爭論。當時占上風的觀點是,徐元慶應該受到表彰,至少應該予以無罪釋放,因為徐元慶是為了替父報仇才走上了殺人的道路。因此,盡管徐元慶殺了人,但他殺人的動機高尚,出發點良好,在講究以德治國的大背景下,朝廷應該赦免徐元慶的罪行。
就在此事將要以這樣的結果落下帷幕之時,陳子昂力排眾議,寫下了一篇《復仇議》,他在文章中說:“今儻義元慶之節,廢國之刑,將為后圖,政必多難;則元慶之罪,不可廢也。何者?人必有子,子必有親,親親相讎,其亂誰救?故圣人作始,必圖其終,非一朝一夕之故,所以全其政也。故曰:‘信人之義,其政不行。’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,仁者不為;以公法而徇私節,王道不設。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,義伏當時,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。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,是奪其德而虧其義;非所謂殺身成仁,全死無生之節也。如臣等所見,謂宜正國之法,置之以刑,然后旌其閭墓,嘉其徽烈,可使天下直道而行。”陳子昂的意思很清楚,徐元慶謀殺之罪,案情清楚,按照唐律當然毫無爭議地應該判處死刑,只有判處死刑才能體現法律的嚴肅性。但是,從另外一個角度上看,徐元慶這樣做卻是為父親報仇,是對父親的一片孝心才讓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,他將殺父的仇恨記在心間,誓與仇人不共戴天,其孝心感天動地,足以令日月變色。因此,陳子昂建議在對徐元慶處以極刑之后還應為他舉行盛大的表彰會,以頌揚他的一片孝心。陳子昂的建議巧妙地解決了“禮”與“法”的沖突,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。最后徐元慶案也就按照陳子昂的建議給了結了。
事情得以如此圓滿地解決,陳子昂難免得意揚揚,他順理成章地要求:有必要將我的《復仇議》“編之于令,永為國典”。陳子昂的要求最后也得到了滿足。然而,幾十年后,陳子昂的《復仇議》就被柳宗元給抓住了把柄。柳宗元認為陳子昂邏輯混亂,大腦不清。柳宗元開宗明義地說:毫不懷疑,陳子昂的建議是完全錯誤的。那么,為什么?柳宗元條分縷析地說:徐元慶一案的要點在于徐元慶的父親是否真的有罪,如果徐元慶的父親有罪,那么被縣尉正法就是罪有應得,父親有罪被誅而徐元慶卻執意為父報仇,謀殺朝廷命官就是十惡不赦的大罪,殺之是題中應有之義;反之,如果徐元慶的父親死于無罪,趙師韞就涉嫌草菅人命,這樣的惡官被徐元慶殺掉也就毫不足惜,徐元慶的行為在客觀上也就是為國除害,徐元慶不但不應被殺,而且還應予以表彰;徐元慶要么有罪,要么無罪,二者只能居其一,一個人決不可能像陳子昂所分析的那樣既有罪又無罪。柳宗元因而斷定,陳子昂的分析看似滴水不漏,實則精神分裂,其本質是核心價值觀念的多元論,陳子昂的建議最終也只能擾亂人心,讓人無所依從。就這樣,陳子昂唯一的一次輝煌記錄被柳宗元給解構了,柳宗元為此還專門寫了一篇《駁復仇議》的文章,并被作為定論收入在了唐朝的法律文獻內。
修竹篇序
東方公足下:文章道弊,五百年矣。漢魏風骨,晉宋莫傳,然而文獻有可征者。仆嘗暇時觀齊、梁間詩,彩麗競繁,而興寄都絕,每以永嘆。思古人,常恐逶迤頹靡,風雅不作,以耿耿也。一昨于解三處,見明公詠孤桐篇,骨氣端翔,音情頓挫,光英朗練,有金石聲。遂用洗心飾視,發揮幽郁。不圖正始之音、建安風骨,復睹于茲,可使建安作者,相視而笑。解君云:“張茂先、何敬祖,東方生與其比肩。”仆亦以為知言也。故感嘆雅制,作修竹詩一首,當有知音以傳示之。
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
丁酉歲,吾北征。出自薊門,歷觀燕之舊都,其城池霸異,跡已蕪沒矣。乃慨然仰嘆。憶昔樂生、鄒子,群賢之游盛矣。因登薊丘,作七詩以志之。寄終南盧居士。亦有軒轅之遺跡也。
北登薊丘望,求古軒轅臺。
應龍已不見,牧馬空黃埃。
尚想廣成子,遺跡白云隈。
南登碣石阪,遙望黃金臺。
丘陵盡喬木,昭王安在哉。
霸圖悵已矣,驅馬復歸來。
王道已淪昧,戰國競貪兵。
樂生何感激,仗義下齊城。
雄圖竟中夭,遺嘆寄阿衡。
秦王日無道,太子怨亦深。
一聞田光義,匕首贈千金。
其事雖不立,千載為傷心。
自古皆有死,徇義良獨稀。
奈何燕太子,尚使田生疑。
伏劍誠已矣,感我涕沾衣。
大運淪三代,天人罕有窺。
鄒子何寥廓,漫說九瀛垂。
興亡已千載,今也則無推。
逢時獨為貴,歷代非無才。
隗君亦何幸,遂起黃金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