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墅記
江北之山,蜿蜒磅礴,連亙數州,其奇?zhèn)バ沱惤^特之區(qū),皆在吾縣。縣治枕山而起,其外林壑幽深,多有園林池沼之勝。出郭循山之麓,而西北之間,群山逶邐,溪水瀠洄,其中有徑焉,樵者之所往來。數折而入,行二三里,水之隈,山之奧,巖石之間,茂樹之下,有屋數楹,是為潘氏之墅。余褰裳而入,清池洑其前,高臺峙其左,古木環(huán)其宅。于是升高而望,平疇蒼莽,遠山回合,風含松間,響起水上。噫!此羈窮之人,遁世遠舉之士,所以優(yōu)游而自樂者也,而吾師木崖先生居之。
夫科目之貴久矣,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艷羨之,中于膏肓,入于肺腑,群然求出于是,而未必有適于天下之用。其失者,未必其皆不才;其得者,未必其皆才也。上之人患之,于是博搜遍采,以及山林布衣之士,而士又有他途,捷得者往往至大官。先生名滿天下三十年,亦嘗與諸生屢試于有司。有司者,好惡與人殊,往往幾得而復失。一旦棄去,專精覃思,盡究百家之書,為文章詩歌以傳于世,世莫不知有先生。間者求賢之令屢下,士之得者多矣,而先生猶然山澤之癯,混跡于田夫野老,方且樂而終身,此豈徒然也哉?
小子懷遁世之思久矣,方浮沉世俗之中,未克遂意,過先生之墅而有慕焉,乃為記之。
“河墅記”譯文及注釋
譯文
長江下游以北的群山,蜿蜒起伏,磅礴雄偉,連綿橫臥于皖、豫、鄂三省好幾個州縣的境內,其中雄奇魁偉秀麗和特別突出的區(qū)域,都在桐城縣。縣城依山而建,城外林壑幽深,有許多園林沼澤的勝境。出城沿山腳走過西北方向的間隙,群山連綿曲折,溪水曲折環(huán)繞,其中有條小道,是供打柴人往來的。轉幾個彎進山,步行二三里,在一條小河的拐彎處,在山巒高聳,巖石壁立的峽谷深處,茂密的林木下,有幾排房屋,這就是潘木崖先生的別墅。我將長袍下擺提起走進去,一泓清流在庭前緩緩流淌,左邊高臺峙立,宅旁參天大樹環(huán)繞。于是,登上高處遠望,田野青碧,一望無際,遠山重巒疊嶂,松濤陣陣,水起波瀾。噫!這就是困頓不得志而避世隱居人士,所賴以優(yōu)游而自得其樂的良宅,而我的老師木崖先生正是居住在這里。
科舉考試被尊貴得很久了,天下讀書人沒有不為之追求艷羨的,早已深入于膏肓、肺腑之中,全都要求得從這里出身,可未必有適用于天下的地方。其中落第者,未必都不是人才;考中的人,未必都是人才。居于上位的人因此而憂患,于是廣泛地搜索尋訪,從而涉及到那此隱居于山林中的布衣之士;而士子中也有趁機通過其他途徑走了捷徑的人,常常可以獲取大官的權位。潘先生名聲傳遍天下三十,也曾與諸生一道屢次參加有司主持的科考。主考官們的好惡與普通百姓不同,常常想著就要高中卻又落第了。一旦放棄并遠離科考,專下心來深入地思考,精心探究諸子百家之書,創(chuàng)作文章和詩歌而傳播于世,世上沒有不知道先生大名的。近來朝廷求賢的詔令屢屢頒下,士人獲得功名利祿的途徑多得很,可先生還是隱跡山澤的清貧之士,與田夫野老打成一片、和睦相處,并將以此種方式安度晚。難道此生只能空手而歸嗎?
在下懷有隱居的念頭已經很久了,可是掙扎在世俗社會的沉浮之中,并不能馬上順遂如愿,經過先生的別墅而頓生羨慕之心,于是寫下了這篇游記。
注釋
江北:這里指長江下游以北地區(qū)。
絕特:超出尋常。
吾縣:指桐城縣。現為安徽省桐城市。
縣治:縣衙所在地,指縣城。
郭:城墻。
逶邐(wēi lǐ):連綿曲折。
瀠洄(yíng huí):曲折環(huán)繞。
奧:深處。
潘氏:潘江,字蜀藻,號木崖,戴名世之師末清初文學家、詩人。
墅:別墅。
褰裳(qiān cháng):將長袍下擺提起。
袱:流水回旋貌。
疇(chóu):田畝。蒼莽:田野青碧,一望無際的樣子。
羈窮:窮困不得志。
遁世遠舉之士:避世隱居、去避遠方的人。
科目:指唐代以來分科選拔官吏的名目。唐代以科舉取士,有秀才科、明經科、進士科等名目,故稱科目。后世即以科目指科舉考試。
上之人患之:一些官高位顯的人對科舉制度的弊端深表憂慮。患,憂慮。
諸生:清代已入學的生員。
覃:深。
間者:官吏名。這里指主考官。
猶然山澤之癯(qú):仍然是隱跡山澤的清貧之士。癯,清瘦。
“河墅記”鑒賞
創(chuàng)作背景
河墅是戴名世老師潘木崖在桐城郊外的住宅。潘木崖在科場屢次失意之后,便放棄了入仕的念頭,隱居于此。作者對此非常羨慕,于是作了這篇雜記。
賞析
這篇散文借記河墅之景,頌揚隱居山林,高潔不污的河墅主人——他的老師潘木崖先生。思想內容十分可取,藝術手法獨具特色。
文章分為三段,首段記游寫景,中段議論抒情,最后統(tǒng)括全篇,卒章顯志。外在形式與思想內容高度統(tǒng)一,實為桐文講究“義法”之范文。文章“因聲求氣”,造句上以四言為主,雜以三,五、七言,既有古歌行韻味,又有韓柳遺風,音律俱佳,字句傳神。如第一段寫河墅眭境,文筆清新優(yōu)美,富有詩情畫意。開頭兩句:“江北之山......多有園林池沼之勝。”是閑大寫意的筆法把桐城河山和盤托出,有如登高鳥瞰,全景盡收眼底。接著避虛就實,去粗取精,細描木崖住宅環(huán)境,如“出郭循山之麓......是為潘氏之墅。”如此由表及里,精雕細刻,還嫌語不驚人,又“升高而望”,用遠景烘托渲染,如“平疇蒼莽,遠山回合,風含松間,響起水上。”近于潑墨。翹首遠望,景色錯落,十分開闊壯觀;側耳靜聽,風嘯水吼,難以捉摸的大自然之聲寫得漸瀝蕭颯,奔鵑澎湃,可聽,可感,可見。至此,大丈夫不遇于時的安適生活環(huán)境描畫得美不勝美。先秦的哲學家荀子在他的《樂論》中說:“不全不粹不勝美。”看來,戴氏對前人的這個美學觀念是心領神會的。他在描寫河墅時,既豐富地全面地表現自然環(huán)境,又去粗取精,經過錘煉、提高、集中,更典型,更具普遍性地表現自然環(huán)境,難愛是很大的。“全”和“粹”是一對矛盾的統(tǒng)一體。只遠望求“全”,不近觀頤“粹”,是自然主義,只講“粹”而不反映“全”,又容易走上抽象的'臣式主義的道路。
《河墅記》的寫作,求全而不失粹,確切地說,是概“全”以精“粹”。如果我們再將第一段把玩一番,我們就會發(fā)現戴氏筆下的河墅,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“龍圖”,云中雖只露出一鱗一爪,然而全貌宛然可見。戴氏把握“全”與“粹”的關系如此之嫻熟,自然得益于桐文的“義法”之說。因為桐城古文義法本身就有兩種意義:“就文之整體言之,則包括內容與形式的調劑,而融合以前道學家與古文家之文論。就文之局部而言之,即專就學文方式而言,則又能融合秦漢派之從聲音證人以摹擬昔人之語言,與唐宋派之從規(guī)矩證人以摹擬昔人之體式”。中國的山水散文萌芽于兩晉,產生于南北朝,鼎盛于唐宋,戴名世繼承了前人記游記景的散文傳統(tǒng),模山范水,體物圖貌,技巧很高,為桐城散文的發(fā)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這篇散文還不同于當時士大夫娛情山水的閑情逸致,風雅倜儻之作,戴氏在這篇文章中棄鋪陳擒藻之常法,求淡描點畫之奇功,其目的在于債河墅之美,贊頌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潔的人格和獨立不群、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質。潘先生應試不第后,從科場回到山莊,托懷玄勝,遠詠老莊,過上清淡、閑適、幽雅的生活,與世俗之徒斷絕了來往,這也是戴氏所傾慕的。在他看來,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場,“與其有譽于前,孰若無毀于其后;與其有樂于身,孰若無憂于其心”。既然科場失意,棄絕了入仕的念頭,“結廬在入境,而無車馬喧”,有何不好。
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議論,情緒激昂,氣勢恣縱,他為先生的際遇鳴不平,矛頭直指貽誤人才的科舉制度。如“夫科目之貴久矣,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艷羨之,中于膏盲,人于肺腑”,寥寥數筆,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態(tài)畢現;而“猶然山澤之瘤,混跡于田夫野老,方且樂而終身”,則贊揚了潘木崖不為利祿所誘惑的高潔風貌。“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,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。”持論公允,愛憎分明,作者在描寫這種超脫塵俗的河墅之中,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氣,深化了自己的思想。
最后“小于懷遁世之恩久矣,方浮沉世俗之中,未克遂意”,升華了文章的主旨。作為一個封建知識分子不逃避現實,為將胸中書數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,歷歲逾時而不罷手,單就這點精神,也是難能可貴的。
戴名世簡介
清代·戴名世的簡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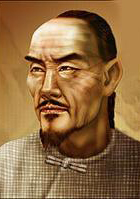
戴名世(1653~1713),字田有,一字褐夫,號藥身,別號憂庵,晚號栲栳,晚年號稱南山先生。死后,諱其姓名而稱之為“宋潛虛先生”。又稱憂庵先生。江南桐城(今安徽桐城)人。康熙四十八年(1709)己丑科榜眼。康熙五十年(1711年),左都御史趙申喬,據《南山集·致余生書》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跡,參戴名世 “倒置是非,語多狂悖”,“祈敕部嚴加議處,以為狂妄不敬之戒”由是,《南山集》案發(fā),被逮下獄。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殺于市,史稱“南山案”,戴名世后歸葬故里,立墓碑文曰“戴南山墓”。
...〔? 戴名世的詩(4篇)〕猜你喜歡
河墅記
江北之山,蜿蜒磅礴,連亙數州,其奇?zhèn)バ沱惤^特之區(qū),皆在吾縣。縣治枕山而起,其外林壑幽深,多有園林池沼之勝。出郭循山之麓,而西北之間,群山逶邐,溪水瀠洄,其中有徑焉,樵者之所往來。數折而入,行二三里,水之隈,山之奧,巖石之間,茂樹之下,有屋數楹,是為潘氏之墅。余褰裳而入,清池洑其前,高臺峙其左,古木環(huán)其宅。于是升高而望,平疇蒼莽,遠山回合,風含松間,響起水上。噫!此羈窮之人,遁世遠舉之士,所以優(yōu)游而自樂者也,而吾師木崖先生居之。
夫科目之貴久矣,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艷羨之,中于膏肓,入于肺腑,群然求出于是,而未必有適于天下之用。其失者,未必其皆不才;其得者,未必其皆才也。上之人患之,于是博搜遍采,以及山林布衣之士,而士又有他途,捷得者往往至大官。先生名滿天下三十年,亦嘗與諸生屢試于有司。有司者,好惡與人殊,往往幾得而復失。一旦棄去,專精覃思,盡究百家之書,為文章詩歌以傳于世,世莫不知有先生。間者求賢之令屢下,士之得者多矣,而先生猶然山澤之癯,混跡于田夫野老,方且樂而終身,此豈徒然也哉?
小子懷遁世之思久矣,方浮沉世俗之中,未克遂意,過先生之墅而有慕焉,乃為記之。
從登香爐峯詩
辭宗盛荊夢,登歌美鳧繹。
徒收杞梓饒,曾非羽人宅。
羅景藹云扃,沾光扈龍策。
御風親列涂,乘山窮禹跡。
含嘯對霧岑,延蘿倚峰壁。
青冥搖煙樹,穹跨負天石。
霜崖滅土膏,金澗測泉脈。
旋淵抱星漢,乳竇通海碧。
谷館駕鴻人,巖棲咀丹客。
殊物藏珍怪,奇心隱仙籍。
高世伏音華,綿古遁精魄。
蕭瑟生哀聽,參差遠驚覿。
慚無獻賦才,洗污奉毫帛。
淡黃柳·空城曉角
客居合肥南城赤闌橋之西,巷陌凄涼,與江左異。唯柳色夾道,依依可憐。因度此闋,以紓客懷。
空城曉角,吹入垂楊陌。馬上單衣寒惻惻。看盡鵝黃嫩綠,都是江南舊相識。
正岑寂,明朝又寒食。強攜酒、小橋宅。怕梨花落盡成秋色。燕燕飛來,問春何在?唯有池塘自碧。
游虞山記
虞山去吳城才百里,屢欲游,未果。辛丑秋,將之江陰,舟行山下,望劍門入云際,未及登。丙午春,復如江陰,泊舟山麓,入吾谷,榜人詭云:“距劍門二十里。”仍未及登。
壬子正月八日,偕張子少弋、葉生中理往游,宿陶氏。明晨,天欲雨,客無意往,余已治筇屐,不能阻。自城北沿緣六七里,入破山寺,唐常建詠詩處,今潭名空心,取詩中意也。遂從破龍澗而上,山脈怒坼,赭石縱橫,神物爪角痕,時隱時露。相傳龍與神斗,龍不勝,破其山而去。說近荒惑,然有跡象,似可信。行四五里,層折而度,越巒嶺,躋蹬道,遂陟椒極。有土坯磈礧,疑古時冢,然無碑碣志誰某。升望海墩,東向凝睇。是時云光黯甚,迷漫一色,莫辨瀛海。頃之,雨至,山有古寺可駐足,得少休憩。雨歇,取徑而南,益露奇境:齦腭摩天,嶄絕中斷,兩崖相嵌,如關斯劈,如刃斯立,是為劍門。以劍州、大劍、小劍擬之,肖其形也。側足延,不忍舍去。遇山僧,更問名勝處。僧指南為太公石室;南而西為招真宮,為讀書臺;西北為拂水巖,水下奔如虹,頹風逆施,倒躍而上,上拂數十丈,又西有三杳石、石城、石門,山后有石洞通海,時潛海物,人莫能名。余識其言,欲問道往游,而云之飛浮浮,風之來冽冽,時雨飄灑,沾衣濕裘,而余與客難暫留矣。少霽,自山之面下,困憊而歸。自是春陰連旬,不能更游。
噫嘻!虞山近在百里,兩經其下,為踐游屐。今之其地矣,又稍識面目,而幽邃窈窕,俱未探歷。心甚怏怏。然天下之境,涉而即得,得而輒盡者,始焉欣欣,繼焉索索,欲求余味,而了不可得,而得之甚艱,且得半而止者,轉使人有無窮之思也。嗚呼!豈獨尋山也哉!
代扶風主人答
殺氣凝不流,風悲日彩寒。
浮埃起四遠,游子彌不歡。
依然宿扶風,沽酒聊自寬。
寸心亦未理,長鋏誰能彈。
主人就我飲,對我還慨嘆。
便泣數行淚,因歌行路難。
十五役邊地,三四討樓蘭。
連年不解甲,積日無所餐。
將軍降匈奴,國使沒桑乾。
去時三十萬,獨自還長安。
不信沙場苦,君看刀箭瘢。
鄉(xiāng)親悉零落,冢墓亦摧殘。
仰攀青松枝,慟絕傷心肝。
禽獸悲不去,路旁誰忍看。
幸逢休明代,寰宇靜波瀾。
老馬思伏櫪,長鳴力已殫。
少年興運會,何事發(fā)悲端。
天子初封禪,賢良刷羽翰。
三邊悉如此,否泰亦須觀。
真州東園記
真為州,當東南之水會,故為江淮、兩浙、荊湖發(fā)運使之治所。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、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,得監(jiān)察御史里行馬君仲涂為其判官。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,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(jiān)軍廢營以作東園,而日往游焉。
歲秋八月,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,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:“園之廣百畝,而流水橫其前,清池浸其右,高臺起其北。臺,吾望以拂云之亭;池,吾俯以澄虛之閣;水,吾泛以畫舫之舟。敞其中以為清宴之堂,辟其后以為射賓之圃。芙蕖芰荷之的歷,幽蘭白芷之芬芳,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,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;高甍巨桷,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;其寬閑深靚,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,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;嘉時令節(jié),州人士女嘯歌而管弦,此前日之晦冥風雨、鼪鼯鳥獸之嗥音也。吾于是信有力焉。凡圖之所載,皆其一二之略也。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,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,其物象意趣、登臨之樂,覽者各自得焉。凡工之所不能畫者,吾亦不能言也,其為吾書其大概焉。”
又曰:“真,天下之沖也。四方之賓客往來者,吾與之共樂于此,豈獨私吾三人者哉?然而池臺日益以新,草木日益以茂,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,而吾三人者有時皆去也,豈不眷眷于是哉?不為之記,則后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?”
予以為三君之材賢足以相濟,而又協(xié)于其職,知所先后,使上下給足,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,然后休其余閑,又與四方賢士大夫共樂于此。是皆可嘉也,乃為之書。廬陵歐陽修記。